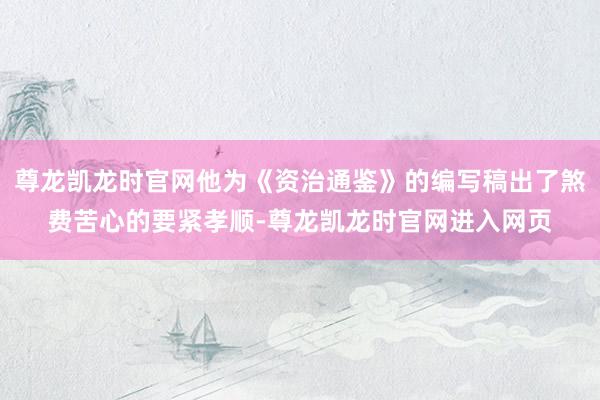
(原标题:六朝往事随活水 但寒烟衰草凝绿——当苏轼碰见王安石(二))
一朝离开了实践政治的繁重话题,王安石与苏轼便有了说不完的共同话语。
五
“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笔墨,闲即俱味禅悦。”(蔡绦《西清诗话》)苏轼此番在金陵共犹豫了一月有半,这是他第一次真实“难分昆仲”——遭受一位资质与才思相配的对话者。两东谈主“剧谈累日不厌”。
要论著述传承,王安石与苏轼都出自欧门。“一代文宗”欧阳修不但我方文才独步寰球,还先后栽种扶携了曾巩、王安石和苏轼三颗中国体裁天外中的瑰丽巨星,他是名副其实的“一生之师”。
也许正是因为这层酌量,王安石再次见到苏轼,坐窝又想起了两东谈主共同的伯乐与恩师。欧阳修曾因不兴奋薛居正等奉旨所撰的官修《五代史》,异常私行又重修了一部。他的这个版块,后世一般称《新五代史》。不知为何,王安石对此耿耿于心,他认为欧阳修应该把贵重的元气心灵才华用于重修《三国志》才对(“恨其不修《三国志》而修《五代史》耳”)。
另有一个未经证据的传言:王安石一向对欧撰《五代史》评价不高。一次,神宗问他:“卿曾看欧阳《五代史》否?”他复兴说:“臣不曾仔细看”,紧接着略带揶揄地说:“但见每篇首必曰一‘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自后有一天,他看到大弟王安国(字平甫)的书案上放着这部书,便问谈:“此书如何?”安国复兴说:“(欧阳公)以理会易晓之言,叙侵略难尽之事。要对它作出准确公允的评价,松弛易。”王安石听了,合计弟弟的话古道而切当。
要是王安石照实贬抑过欧氏《五代史》,放到后东谈主的视域中,则此事一方面折射出这位目无余子的“拗相公”的孤傲与不自谦,另一方面却也展现了他对史学的深入融会。莫得东谈主怀疑欧阳文忠公冠绝古今的文才,但史实疏简而议论太多,确切是历代学者对其《新五代史》的共同微词。
至于王安石为什么认为重修《三国志》更为垂死?我臆想,欧阳修虽曾经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治的宰执高位,但他是典型的文东谈主,但愿从刚刚拆伙的五代十国纷乱历史中招揽履历申饬,以期有补于治谈。而王安石虽是一位涓滴不逊于欧阳修的伟大体裁家和学者,但他对政治的自我盼愿更高,官也作念得更大,因而他更着眼于实践:其时,华夏汉东谈主的宋、契丹东谈主的辽和党项东谈主的夏三分寰球,与魏、蜀、吴三国时间颇有相类之处。这即是王安石认为重修《三国志》才是当务之急的根源,他将重修《三国志》行动挥写一篇针对样貌的策论。
不论如何,如今世间已无欧阳修,王安石的期待当然而然落到了咫尺这位欧阳修身后最胁制的文学界巨子身上。他对东坡说:“子瞻当重作《三国书》。”没猜测苏轼一口回绝:“我老了,同意保举刘谈原,他是比我更胜任的东谈主选。”
苏东坡向王荆公保举的这位刘谈原,大名刘恕,谈原是他的字。他关联词王安石的多年旧友了。《宋史》本传称,“恕少颖慧,书过目即成诵……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除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陡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
提及刘恕,他还以鲠直抵御、论东谈主之短无所隐而广为东谈主知。刘恕年青时与王安石交情深厚,后者在野后,专为鼓吹变法而建筑制置三司条例司,第一个想要升引的即是他。然而刘恕先以我方不熟悉财政治务为由绝交,进而劝告往日好友,当以尧舜之谈辅佐目前皇帝,“不应以利为先”,后又批评了新法的诸多“分手众心者”。这以后,他还屡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迎面顶嘴王安石,令这位权倾一时的在野者下不了台。王安石的党徒们对他咬牙切齿,而友一又们则时时为他捏一把汗。
不啻如斯,刘恕对王安石十分自夸的“新学”也很不买账,每遭受有士子酌量(安石)新经,他便会气喘如牛:“此东谈主口出邪言,面带妖气。”可能是出于对他屡屡“面折王介甫”的信服,苏轼曾赠诗刘恕:“孔融不愿让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时东谈主认为这句诗亦然在讥笑王安石。不外王安石身为丞相,毕竟亦非小肚鸡肠,虽说刘恕让他很不欢笑,但他也没拿这位往日好友如何。他遭受刘恕时,最多也即是尖刻地戏谑:“谈原读到汉八年未?”意指刘恕读史,沉溺于繁琐败兴的细枝小节,不可穷经达理。
六
即便按宋东谈主习尚的虚岁来计,元丰七年这一年,东坡也不外刚49岁辛勤,远莫得熟练写不动书的地步。这昭彰仅仅个藉端。真实的原因,十多年后苏轼从海南岛北归途经南康军(今江西庐山一带)时,曾亲口对刘恕之子刘义仲(字壮舆)和盘托出过。
传闻,刘义仲摄取家学,也精于史学,他曾经从欧阳修《新五代史》中选录出广大讹误,成《纠谬》一书,还曾专门呈送苏轼。东坡因此钦慕:“夫为史者,汇聚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是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此事似乎还从一个侧面施展了,王安石对欧公《新五代史》评价不高,并非绝不测思意思。
当苏轼向王安石保举请刘恕重修《三国志》的时候,这位一代良史正全身心性投身于另一项注定将会永恒的要紧行状——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这项“国度工程”前后接续19年,早在神宗之父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便已启动推敲。那时英宗专门设局编修,并授权司马光,不错自行在馆阁英才中挑选任何东谈主作念助手。司马光则对皇帝说,非刘恕不可。由此不错想见,刘恕一定是那时公认的“史学第一东谈主”。这在另一方面还折射出那时这批名士的多元往来酌量:昭彰,司马光作为王安石后生时间的知己,他与刘恕的交谊一定也不浅。而刘恕的行状照实极为过劲,在《资治通鉴》的编纂经由中,凡“纷错难治”的史实,大多由他条分缕析加以梳证。尤其是,身为那时的“近代史”威名,《通鉴》中魏晋以后的史实阅兵行状透顶是由他完成的。
不论如何,苏轼固然莫得允诺王安石,但却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头。临终前不久,他又留神地把这项行状传递给了刘义仲:“盖介甫以此事付托轼,轼今以付壮舆也。”
然而,重修《三国志》一事到此就没了下文。
值得红运的是,王安石抑或苏轼,这两位伟东谈主都没能作念成的事,由另一位伟东谈主作念成了,况且正是在刘义仲之父刘恕的协助下作念成的。他所达到的竖立远远卓越了单纯重修一部《三国志》——正是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得宠,让他的头号政敌司马光投闲十六年,竖立了一代史学泰斗和一部史学经典。
在这件事上,随纯粹便的宋东谈主条记又给咱们留住了一个不可能梳理得澄莹的大坑:刘恕并莫得活到苏王金陵相会的那年,他卒于元丰元年(1078),年仅47岁。自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出判西京御史台,刘恕跟班温公赴洛阳修书,前后凡八年。他为《资治通鉴》的编写稿出了煞费苦心的要紧孝顺,但我方却没能看到它终末完成。《通鉴》的成书,是在他身后七年。因此,按《邵氏闻见后录》之类条记之说,迟至元丰七年,苏轼仍向王安石保举刘恕,几乎是离奇乖癖——作为共同的故交,王安石和苏轼都不可能不知谈刘谈原早在七年前就已离世。退一步说,即使咱们把苏轼向王安石保举刘恕之事提前到后者辞世时,也即是最晚当在元丰元年,粗略也说欠亨。因为那时苏轼才40岁刚出面,说什么“某老矣,愿举刘谈原自代”,岂非言三语四?更不可念念议的是,刘恕实质上还比苏轼年长五岁!
宋东谈主对于此事还有另一则不同记录,没准更接近真相,载于朱弁《曲洧旧闻》卷五:
东坡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功德甚多,谈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曷不为之?”坡曰:“某虽工于话语,也不是当行家。”
似乎重修《三国志》是刘恕我方的心愿,后东谈主不知因何把它按到了王安石头上。不外,这些不同纪录在少量上是基本一致的:苏子瞻学士虽为寰球东谈主景仰,但他对于我方的资质口角有着相配领路和准确的厚实。
就连苏轼这样的远古天才,对于证据着实亦然满怀敬畏之心。
正如王安石认为重修《三国志》非苏轼不可,苏轼也绝不惜啬地对王安石的史才打出了最高分。早在熙宁元年(1068),朝廷以宰相曾公亮提举,修撰刚刚驾崩的宋英宗《实录》,那时如故翰林学士的王安石自请承担这项行状。他不要助手,独自一东谈主完成了30卷《英宗实录》。苏轼自后对刘义仲说:“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
七
尽管王安石和苏东坡在政治态度上永久处于对立的两个阵营,但在体裁规模,他们却时时彼此观赏、惺惺惜惺惺。
对于政治态度、个东谈主品格与学识才华三个不同的层面,宋东谈主比咱们今东谈主要分得澄莹得多,他们十分自发地致力不把三者搅合到一皆。至少,他们中的第一等东谈主物很少会让政治态度傍边私东谈主间的友谊、异化对诗文的品鉴。在这点上,宋代、尤其是北宋士医师展现了只有欧洲发蒙洞开以后才萌发的那种惊东谈主的“当代厚实”。这样的风采,足以给当代中国学问分子结巩固实地上一课。
熙宁八年(1075),与范仲淹皆名的有宋一代名相韩琦升天,苏轼应其子韩忠彦之请,作《醉白堂记》一文(“醉白堂”是韩琦为我方的洛阳私宅取的名字,以示我方对唐代大诗东谈主白居易的追慕。)韩琦在早年担任扬州官职时,是后生王安石的第一任上级。自后,他坚决反对变法,成为宰相王安石最苍劲的敌手。两东谈主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王安石读到这篇著述后开打趣说:“此韩白优劣论尔。”话传到苏轼耳朵里,他坐窝反唇相稽:“不若介甫《虔州学记》,乃学校策耳。”
元丰元年(1078),时在徐州知州任上的苏轼适时任杭州知州赵抃之请而作并亲书《表忠不雅碑》(此碑被誉为苏东坡“四大名碑”之首,现有有明嘉靖拓本),以寥寥数百言,赏赐了五代时期钱氏三代国主在吴越国消弭兵戈,安堵东谈主民,最终纳土归宋的事迹。王安石拿到苏轼的这篇著述后,一直把它放在座椅边上,那时叶涛(字致远,王安石弟安国之婿)、杨德逢(笔名湖阴先生,王安石晚年隐居金陵时的邻居及友东谈主,安石曾有多首诗题赠于德逢)二东谈主在座。有个食客兴趣地问:“相公你也心爱此东谈主的著述?”王安石复兴说:“这篇实在太像西汉著述了!”随后他又笑问:“那么像西汉的谁呢?”杨德逢无须婉言:“王褒”。王褒字子渊,笔名桐柏真东谈主,是汉宣帝时间一位出名的辞赋家。王安石说:“不可草草酌量。”杨德逢又说:“那么是司马相如和扬雄之流吗?”王安石复兴谈:“司马相如的赋、扬雄的文,叙事之典雅富华丽莫得达到这篇著述的水准,它可与司马迁飞奔陡立了!”于是满座都对它赞誉不已。然而王安石仍不甘休,陆续追问:“它究竟像司马迁的哪篇著述呢?”世东谈主一时不知所措。只见荆公徐徐谈来:“《楚汉以来诸侯王年表》也。”
无人不晓,唐宋“古文洞开”所言之“古文”,即先秦两汉之文。古文家的写稿一直以此为准绳,他们称一篇著述像西汉著述,那即是最高褒扬。早年王安石还曾赞好意思司马光的著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谪贬黄州,隐居钟山的王荆公对他的关怀反而更多了,他时时主动探听东坡的信息。一日,有客自黄州来,荆公问:“东坡近日有何趣话?”宾客复兴说:东坡近日梦后醒来,写了篇《成都圣像藏记》(亦名《宝相藏记》),一气呵成千余言,我船上正巧有写本。
王安石坐窝让东谈主取来,那时已到夜里,月出东南,林影在地,他站在微风习习的屋檐下,迫不足待地展读,喜上眉梢。他读完后说:“子瞻,东谈主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宾客向他求教,他说:“文中有一句‘如东谈主善博,日胜日负’,不如写成‘如东谈主善博,日胜日贫’。”自后苏东坡得知此事,不禁抚掌大笑,深以为然。据苏轼之孙苏符说,这句话苏轼第一稿写的正是“日胜日贫”。而在传世的苏轼文聚首,这句话也确切遵王安石提议改成了“日胜日贫”。要是他说的不假的话,施展两东谈主在对笔墨的把抓方面心有灵犀。
潘淳的《潘子真诗话》和惠洪的《冷斋夜话》将这两则文学界佳话刻画得娓娓而谈,令东谈主有将心比心之感。但将它们收录于《苕溪渔隐丛话》的胡仔却抒发了我方的质疑,他认为,熙宁间王安石当国,力行新法,苏轼写了那么多诗文不遗余力地加以批评和讥笑,王安石岂肯胸无芥蒂?想必也不可能那么心爱东坡的著述。“今冷斋与子真所笔,恐非其实。”
胡仔是北宋末、南宋前期东谈主,他的念念维阵势很彰着地受到了北宋后期尖锐化的党争以及南宋一朝魔鬼化王安石念念潮的侵蚀,照旧很难感受北宋士医师之间那种率直荡的正人交游之谈。伴跟着政治谈德的日益劣质化和半壁山河的沦丧,宋东谈主的襟怀也一天比一天局促,心扉也一天比一天萎缩。
自后的历史还告诉咱们,这不仅仅仅宋代,还号称悉数华夏时髦历程中的里程碑式的障碍,就发生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的那几十年间。
八
很可能,早在苏轼作为王安石变法最热烈的批判者之一活跃在官场之时,二东谈主就有过隔空附和的佳话。
熙宁七年(1074)末,苏轼知密州任上曾有诗《雪后书北台壁二首》,用到了“盐”“麻”“叉”“尖”等韵脚。也许因为这几韵是历来诗东谈主很少用到的险韵,激起了王安石的好胜心,他有《次韵子瞻赋雪二首》。而东坡见到荆公的和诗后,又有《谢东谈看法和前篇二首》。王安石则再复《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如斯往复几个回合,竖立了宋诗史上一则为后东谈主津津乐谈的好意思谈,即所谓“苏王险韵赓和”。
苏轼和王安石的这组《雪》诗写得究竟有多好,近千年来诗评界众说纷繁,但它们的用韵之难却是东谈主所共知。以致于从“苏王赓和”诗问世以后,宋、明、清每个朝代都握住有诗东谈主加入附和,可惜无不是勉强拼集辛勤。南宋大诗东谈主陆游说得很中肯,“(像这样顶尖的笔墨比拼)议者谓非二公莫能为也”对此,他自叹弗如,“予固好诗者,然念书有限,使劲鲜薄……有愧辛勤。”南宋末年,江西诗派诗东谈主方回则对此次苏王之间的“诗歌比赛”作了一个明确的裁决:“无意用韵甚险,而再和尤佳……虽王荆公亦心折,屡和不已,终不可压倒……非坡公天才,万卷书胸,未易至此。”到底是一个终年在诗歌寰宇里摸爬滚打的东谈主,深谙作诗押韵的一般规矩:像“盐”“麻”“叉”“尖”这类险韵,无意用一下,未必不可无心得之,但有厚实一和再和,要想写出好诗就极难了。
在这一次的较量中,不论王安石是否真如方回所言的那样“心折”,他使出终生才华终究没能压倒苏轼,却是事实。另据《苏轼诗集会注》卷十二:“世传王荆公尝诵先生此诗,叹云:‘苏子瞻乃能使事至此!’时其婿蔡卞曰:‘此句不外咏雪之状……’荆公哂焉。谓曰:‘此出谈书也。’”
按常理,王安石的第一次和诗以及苏轼与他之间的往来再和,都应作于苏轼原诗写出不久,不太可能事隔五六年、发生在“乌台诗案”以后。很可能,那时王安石尚在宰相任上,也即是他们之间政争最尖锐化的那段时分。这就充分施展了上述胡仔的酌量即便不是“以小东谈主之心度正人之腹”,亦然“以庸东谈主之心度英杰之腹”。
对于苏轼这组《雪》诗的话题还没完。
传闻,这组诗问世后,读过的东谈主当中莫得一个能解其意。因为诗中有这样一句:“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大家都不知谈“玉楼”“银海”是什么意旨意思意思。如今他来到金陵,终于遭受了老友。王安石迎面问东坡:“谈家把两肩称为‘玉楼’,把眼睛叫作‘银海’,你用的是这个意旨意思意思吗?”东坡会心一笑。自后私行里对好友叶涛说:“可惜啊!世上那么多王荆公的徒子徒孙,可谁能有他这样博学的!”
其实,就拿这位叶涛来说,因为他曾跟班王安石傍边,在政治上昭彰属于维持变法的新党。他自后还投合宰相曾布,绍圣间(1094—1098)曾官居中书舍东谈主。叶涛颇有诗名,与苏轼交谊甚厚,酬唱也不少。他的远房亲戚蔡京当国后,叶涛还因此上了“元祐党籍”黑名单。阿谁时间士医师之间的全球酌量与私东谈主交情,在当代东谈主看来实在是难以贯通!
王安石于英宗治平年间寓居金陵服母丧并讲学时,曾作过一首《桂枝香·金陵怀古》词:
登临送目,正祖国晚秋,天气初肃。沉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银河鹭起,绘画难足。
念往昔,旺盛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往事随活水,但寒烟衰草凝绿。于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咱们都知谈,词是东坡的透顶坚强,王安石不以此见长,留住的词作也未几。但当东坡读到这首词后,也忍不住叹气:“此老乃野狐精也!”自后南宋民间有传言,煞有介事地说王安石是天上狐仙下凡,看着手头灵感多半来自东坡先生的这声钦慕。
《西清诗话》中另记一事云:东坡在金陵时,王安石拿出我方的最新作品请他品鉴。其中有一首《寄蔡氏女子》,是写给我方男儿也即是蔡卞之妻(世称“七夫东谈主”)的。当东坡读到“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两句时叹谈:“自屈(原)、宋(玉)没,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王安石也不自谦,纵脱不羁地说:“非是子瞻言不赤忱助威我,我亦然这样自夸的,只不外从未与庸东谈主俗子提及过辛勤。”
确切,罕见能手之间的共识,是芸芸众生无法贯通的。
北宋末期,闻明诗僧惠洪将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三东谈主列为“本朝诗东谈主”的前三,他在《冷斋夜话》一书中不啻一次拿三东谈主的诗作相比。据他纪录,苏轼曾评答复,王安石晚景的诗真实达到了最好田地,而他的五言律诗最好,绝句次之,七言律诗则终究没能卓越“晚唐气息”。
被苏轼批评为“最胜”的“荆公晚景诗”,正是王安石卜居金陵的十年间所作,苏轼的考查恰好也即是发生在这技艺。其实,苏轼我方一生体裁创作的黄金岁月,恰好亦然在这段时期谪居黄州时。统一时期,渐渐起飞的还有黄庭坚、陈师谈、张耒、晁补之等一多半诗坛新星。
咱们应该记起北宋时期的“元丰”年号,它记号着中国诗歌史上继王维、李白、杜甫活跃的大唐开元、天宝年间之后的又一岑岭。
